俱乐部动态
星罗·棋布——自称“无所作为”的王绶琯老大爷,您还想咋?(二)
时间:2021-01-18来源:
昨天的文章一直到晚上9点半才发出去,里面提到的说王绶琯老大爷像Master Wugui 的那位哥们看到了,分享到了他们青少年俱乐部老会员的群里。
于是今天早上,俱乐部队秘书长周琳老师和王老的女儿王荧先后发微信过来,表示已经读过啦。
得,这下子彻底打消了我偷懒拖稿的念头,还是乖乖接着写吧。
顺带提一句,其实昨天除了王绶琯老爷子过生日之外,我和同事一起采访过的红旗-7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总师钟山院士也恰逢90大寿,给他老人家发了短信,恭祝他生日快乐,寿比南山。

一直希望能去这位老先生家里看看他养的四只猫,据他兴高采烈地跟我们介绍,这几个家伙性格各异,而他平常主要负责喂和玩(估计铲屎另有专人负责),以及保护其中胆子最小、常被欺负的那只……
钟山院士的节目是台重点片《总师传奇》系列中的一集,从2018年开始正式拍摄,至今还在保密审查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与观众朋友们见面,我这个执行总导演一直在为之忙碌,头发都快愁白了,555。
今天早上在朋友圈里看到西南联大校友会的老师转发的一则新闻,才知道我2009年采访过的马识途老爷子——也就是《让子弹飞》的原作者、西南联大在世校友中最年长的一位、老地下党、著名革命作家和书法家——昨天恰好也过生日,他老人家这个日子是按阴历算的,难怪我没记住。

这位人生极富传奇色彩的老先生如今周岁106了,“状态非常好”,三年前他打败了肺癌,去年还是前年刚刚封笔,现在的愿望是活到今年7月1日,亲自为我党的百岁寿辰庆生……我觉得以他无比顽强的生命力,一定能稳稳当当地如愿以偿。
关于马老的文章,我之前零零散散写过,忘了是写到第三部分还是第四部分了,回头找个机会再接着填自己挖的这个大坑,嘿嘿。
书归正传,接着讲王绶琯老大爷的故事。
昨天既然说到了他当年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——有人将之称为“舍舟问天”——那么今天的段落,就要从他如何驶入人生的正轨说起。
在改行这件事上,最先给他鼓励的,是在英国结交的几位朋友,特别是一位60岁的丁大夫,建议他朝着一向热爱的自然科学方向去努力,而他也真的从善如流,动了心。

从1949年开始,王绶琯给几位英国天文学家写信,交流学科相关的情况。后来就时常坐车去离格林尼治不远的伦敦大学天文台,与台长格里高利聊过几次,表现出想去那里工作的愿望。
当时,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隔壁邻居格林尼治天文台也归海军管辖,虽然是近水楼台,作为中国留学生,王绶琯并不具备“先得月”的条件,而伦敦大学天文台则拥有一个60厘米的望远镜,是英国当时最大、最好的天文观测设备,能用它来做研究,自然也是一桩美事。
格里高利是一位60多岁的老科学家,他对于从中国远道而来、有志于天文学研究的这个年轻人表示了赞赏和鼓励,不仅予以无私的指导,还在1950年接纳他进入天文台工作,遇到这样的“贵人”,实属幸运。
能不能用两三年的时间,变成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呢?王绶琯想试试看。
这位自称“无所作为”的祖宗,当年还真是……敢想敢干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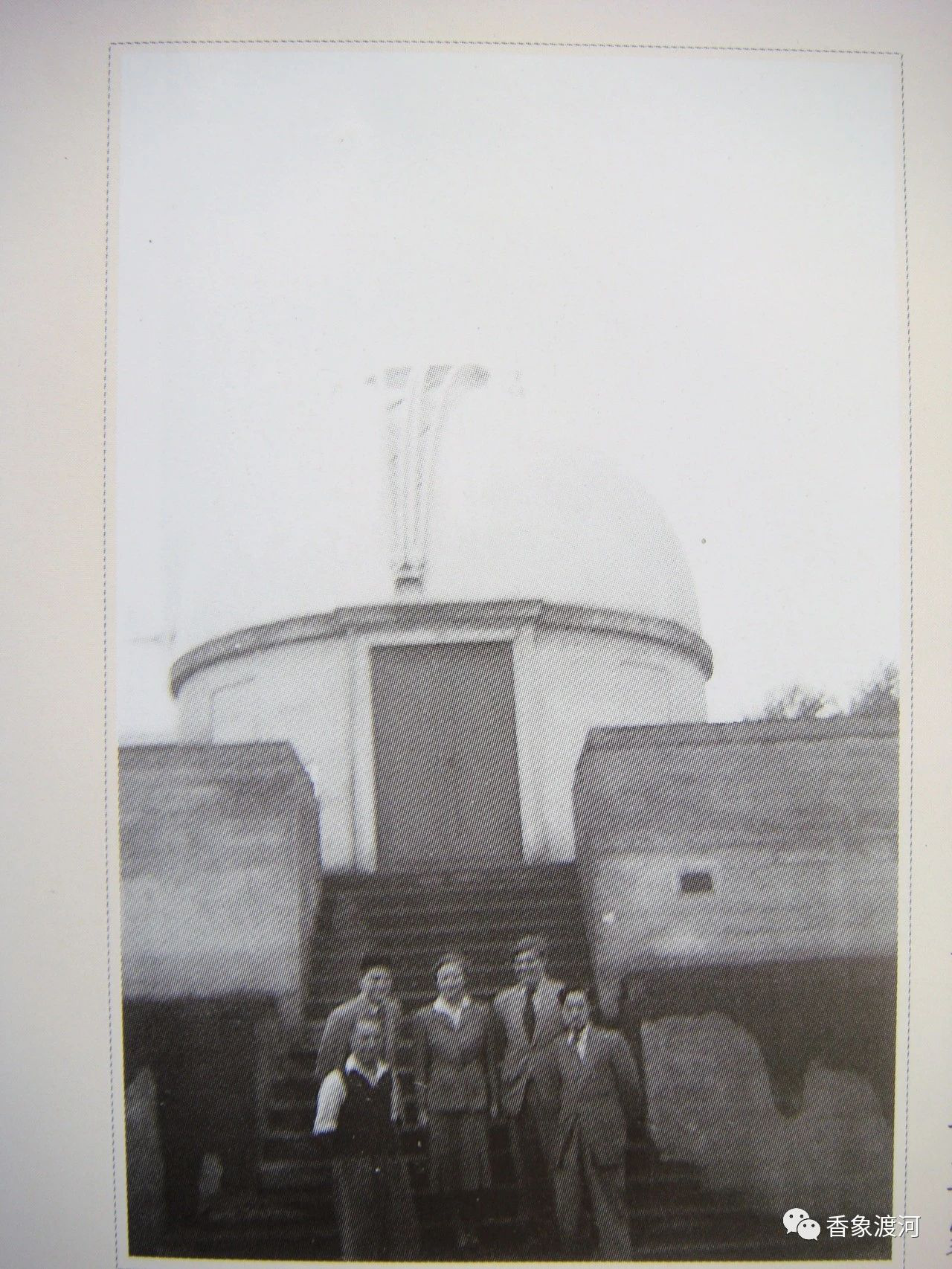
从1950年到1953年,王绶琯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夜夜观星,充分享受着天文学的乐趣,在2019年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报道中,摘抄了他在《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》一文中的若干文字:“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,地处伦敦西北郊,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,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,很宽很直……黄昏后,夜色罩下来,朦朦胧胧,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,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……”
不过,当王绶琯的目光投向无垠宇宙时,他的心却一直牵系着家乡故国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,让很多当时在海外工作、求学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,在之后的几年里,他们毅然抛下了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丰厚的待遇,顶着压力甚至冒着风险,回来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。

1952年,王绶琯给紫金山天文台写信,想问问国内还搞不搞天文:
“因为紫金山天文台,原来解放前就有了,余青松先生在做了。后来才知道余先生到美国去了,当时张钰哲先生在负责,结果就收到张钰哲先生的信,说叫我赶快回来,现在中国要发展天文了。”
了解到国内急需天文领域人才的情况,翌年,这个半路出家的游子就踏上了归途。
那么当时的他,算是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了吗?
至少归国初期的履历是这样的:
1954年,参与修复紫金山天文台60厘米望远镜;
1955年,在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完成提高我国授时精度的任务;
1958年,在北京天文台开始了对射电天文学的探索,成为中国该领域的奠基人……
看起来,好像应该算吧,哈哈。

所以一位天文学家的住所,会是什么样子的呢?
2016年去采访的时候,王绶琯老爷子住在著名的黄庄小区,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中国科学院的老先生的家也在那里,比如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、力学家郑哲敏院士,空气动力学家俞鸿儒院士,植物学家王文采院士……
他家楼上,就是已故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的家,后来有一次还被我们借用,一口气拍了八个外采——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心中忐忑,总觉得自己实在很能给人家添乱。
从2016年4月22日第一次拜访算起,我大概去过王老爷子家六七次,他家的客厅很大,东西满满当当,不时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陈设。
沙发旁边有一个晶莹剔透的LAMOST天文望远镜的模型,透露着他的身份与成就,而鲐背之年的他只要往那儿静静地一坐,就是妥妥的大家风范。



每天下午,屋子的阳光比较好,这位老大爷就能坐在沙发上,跟你慢悠悠地聊会儿天,有时候思维有点儿发散,在旁边陪着我们采访的女儿王荧就想办法帮他把话头拽回来,生怕他聊多了累着。
记得跟我第一次介绍他女儿时,老大爷说:这是王荧,是我的保护神。
嗯,保护得好极了——一会儿给戴着助听器、但有时依然听不清楚的他翻译我们的话;一会儿摸摸他的“小爪”是不是冰凉,看需不需要休息;一会儿拿血压计量量飙升到多少了,该吃药就安排吃药;一会儿扒根香蕉喂他吃,让他补充点儿能量;一会儿跟他说说笑话,父女俩的幽默,总让人忍俊不禁……

最逗的是初次见面,老大爷跟我说起他早年接受某媒体采访的经历,说人家先后来过两次,第一次看着“也蛮穷的样子”,第二次就“比较阔气了”。
王荧很不服气地说:“你怎么看出人家没钱的啊?”
老大爷笃定地回答:“这不用看,感觉。”
不知道在他老人家的感觉里,我们这个摄制组算是穷还是阔气,哈哈哈。
包括说起他晚年折腾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事,除了深谋远虑、润物无声的种种筹谋和布置之外,其实好玩的梗也挺多。
比如到底要不要叫“俱乐部”,似乎就纠结了很久。
老大爷自己显然很喜欢这个叫法,他有意让参与其中的青少年们感觉更轻松,更有乐趣,觉得最好做成俱乐部或者沙龙那样的活动,可听说如果是正式的社团组织就不宜用这个名头,就有点踌躇:“我不是搞经济的,法人到底有多重要我不知道,孩子们在一起玩到底要不要法人管啊?”
再一想,叫俱乐部,“会不会让人想歪了,你是搞卡拉OK什么的。”
噗哈哈,老大爷您想多了。

后来据说是为了能够行得通,他们这个组织的真正名字被定成了“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”,老大爷一本正经地跟我讲笑话:“不过是委员长比部长要大一点,俱乐部只能当部长,委员会就可以当委员长。”
喂,不要说得您跟官迷一样呀~
玩笑归玩笑,其实老大爷在折腾这件事的时候,野心真的挺大的,可不只是“当委员长”这么一个小目标而已。
我经常说他是在下一局大棋,而这也是我题目中“星罗·棋布”这个词的用意所在:“星罗”指的是他毕生潜心于天文学研究工作,“棋布”则是指他晚年在青少年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方面谋篇布局。
老大爷跟我讲:“我是搞天文的,地球现在四十六亿年了,王荧查了,从动物开始是二十八亿年了,人类是很新的一种动物,大概几百万年吧,我们这个文明社会到了信息时代才二十几年。所以我们觉得能够看得清楚三十年、五十年就很不错了,从三十年、五十年来看中国教育,素质教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”
这个参照系……我就说吧,跟普通人比起来,天文学家的眼光总会更为长远,因为他们的标尺压根儿就不一样。

而老大爷在替国家操心未来三五十年的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时,我总觉得他的出发点或是源动力,还是要追溯到三五十年前他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他会对曾经遇到的帮自己指明方向、改变命运的“贵人”们深深感激,也一直遗憾于没能更早地接触科研道路上的良师益友——“我可能正因为老觉得(自己)这方面有些缺陷,所以就觉得特别可贵一点”。
他知道人才的成长和科学的成就,很多都跟机遇有关,而对于青少年来说,想要把握住这些机遇,往往需要长辈、导师施以援手。
“在物理界或者说生物界,一切充满机遇,我们每个人存在都是几万亿分之一的存在,那么你会在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;一个人成功的事业,作为我们新闻记者,或者历史学家,或者小说家,把它写下来、记下来,你再去看看这当中每一个人物,都是非常稀有的机遇;每一件事情,贾宝玉去找林黛玉也是非常奇怪的机遇。所以王国维是看到这个了,他那个很有名的三段论,第三段就是机遇,对不对,他本来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了,忽然一下子豁然开朗。”

那么,当自称“无所作为”的他老人家,终于有能力扮演引路人的角色,可以在关键时刻拉孩子们一把的时候,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?
这件事情,容我明天再好好讲一讲。
想起当年每次去采访王绶琯老大爷,到了结束告别时,他都会坚持亲自把我们送到电梯口,按他女儿王荧的说法:这是我爸的“十里长亭”。
当时自然是由衷感动,现在想想自己搞这种拖拖拉拉的文章连载,倒也有点子“十里长亭”的意思了,哈哈。

朱大象个人简介
朱童,纪录片导演,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,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《大家》栏目工作十余年,采访各领域“大家”数十位。

